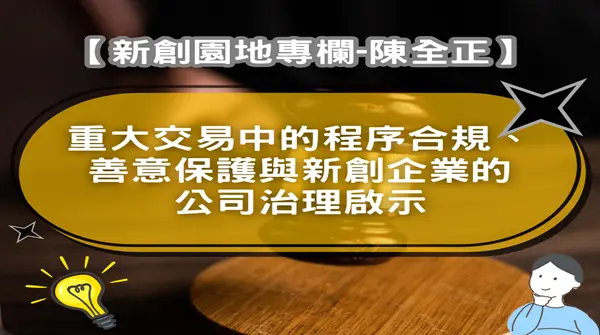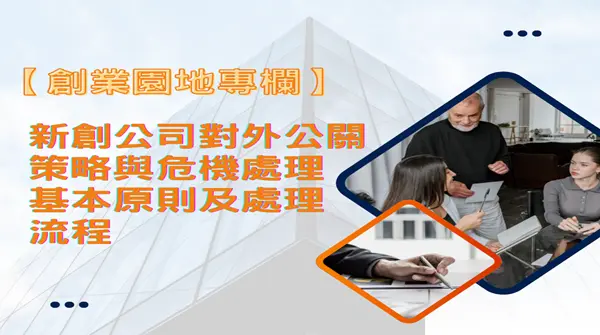【新創園地專欄-黃沛聲】從臺灣企業併購法三修草案,觀察產業控股公司的轉型策略
走過資訊透明與少數股東保護的修法階段,臺灣企業併購法(以下簡稱「企併法」)在 2025年提出第三度修法草案,正式將視野推向「擴大產業規模」與「強化國際競爭力」。這不僅是一場立法更新,更是臺灣產業面對全球經濟重組,即美國川普政府帶起「反全球化」及「保護主義」浪潮下的生存戰略。

走過資訊透明與少數股東保護的修法階段,臺灣企業併購法(以下簡稱「企併法」)在 2025年提出第三度修法草案,正式將視野推向「擴大產業規模」與「強化國際競爭力」。這不僅是一場立法更新,更是臺灣產業面對全球經濟重組,即美國川普政府帶起「反全球化」及「保護主義」浪潮下的生存戰略。
從過往修法到「產業控股公司時代」
臺灣《企業併購法》自 2002 年上路以來,歷經兩次重大修正,2023 年的「第二次修法」已引入「稅中立」制度,以及收買請求權等保護機制,提升中小股東的權益保障。但這些改革多半圍繞在程序簡化、資訊揭露與股東保護,仍未能觸及企業「主動整併」與「集團化升級」的核心誘因。
2025 年「第三次修法」的最大轉向,即是呼應臺灣產業的實際困境,從「消極防弊」轉向「積極促進」,以強化企業進行控股整合的誘因結構。尤其以工具機、機械、水五金等製造業為例,這些產業雖為臺灣出口支柱,卻多屬中小型分散經營、缺乏整合規模。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之下,唯有透過成立控股公司、集中資本與決策及整合集團資源,方能提升研發能量與全球佈局能力。
為此,修法特別設計第 44-2 條,明定企業如因控股整併產生證券交易所得,可選擇不計入當年度基本所得額,延後至實際轉讓時再行課稅。此一設計,即在於排除最低稅負制(AMT)干擾,減輕企業進行股權整併時的財務壓力,讓集團化升級從「政策口號」真正走向「制度落地」。
此舉背後的戰略意圖非常明確,就是要讓臺灣產業能更快速組成具國際競爭力的集團,以「產業控股公司」為平台,整合資源、縮短決策鏈,應對全球快速變局。
產業規模經濟,為何是現在?
臺灣過去在全球化浪潮中,是靠著製造代工與國際分工模式建立優勢。然而,近年反全球化的兩股浪潮:「碳中和政策」與「國安自主戰略」,正快速重塑產業規則:
1. 碳稅與近地製造
在全球暖化的趨勢下,國際分工的產品需要進行長途的運輸,因此衍生的產品碳足跡迭遭批評。以歐盟為首之政策力推在地化供應鏈,從而過去靠全球運籌的臺灣代工商業模式,面臨挑戰壓力。
2. 國安與製造回流
在 COVID 之後美國重啟「美國製造」政策,對於半導體、醫療、軍事供應鏈皆要求「地緣安全」,過往依賴海外供應的策略正遭重新審視。
這些浪潮對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臺灣產業結構,已形成實質衝擊。多數中小企業缺乏跨國運籌與轉型能力,尤其接續面對關稅政策壁壘的挑戰,若不整合將難以單兵突圍。
本土案例:聯電五合一,製造業控股整合的原型實驗
2000 年聯電推動的「五合一併購」案,是臺灣半導體業首次以控股概念完成企業重組之案例。聯電原本與旗下三家子公司(聯誠、聯嘉、聯瑞)及合作夥伴合泰,在代工製程上各自經營、彼此分工。但當全球半導體進入規模競爭與資本密集化階段時,聯電意識到若持續多頭經營、重複資本投資,將不利全球競爭。於是啟動股權整併,透過現金增資、技術作價與股權交換,於短時間內完成「五合一」,集中決策與研發能量。
這場併購的本質,是以「技術+資本」作為交換籌碼,達成集團治理整併與上下游流程整合。儘管當時尚無《企業併購法》,聯電仍成功在法制空窗中完成架構調整。若此案發生於今日,有了第三次修正草案之第 44-2 條的稅務排除與 52-1 條的少數股東權處理機制,整併效率與股權調整過程都將更為順暢,也能降低潛在司法爭議風險。聯電的整併成功說明,當產業進入資本密集與國際競爭階段,企業若能預先建構控股型治理架構,不僅能快速應對市場變化,也為後續國際資本操作預留彈性空間。
本土案例:大聯大控股,整合不合併的台式聯盟戰略
2005 年,由文曄、品佳、詮鼎與富威等四家電子零組件通路商共組「大聯大控股」,開啟了臺灣產業罕見的自主控股整併模式。相較於過往多數由大企業主導的併購,大聯大的成型過程更像是一場「同業聯盟」。這四家公司原本彼此競爭,但在全球電子供應鏈分工深化、品牌端要求全球化協作的背景下,零組件通路商產業能選擇以控股平台形式合組大聯大,實現集中採購、統一品牌窗口、共享物流與財務資源,確實有大智慧
整併方式並非單純吸收式合併,而是保留各子公司的經營自主性,並在控股公司層設置協調機制與資源分配權限。這種「鬆合型整合」模式,有效平衡了整併效率與創業家股東的主導權,具備高度延展性與操作彈性。若能套用現行《企併法》第三次修法草案中的第 44-2 條與 52-1 條,大聯大式的控股組織將能獲得稅務中立與法律程序簡化的保障,進一步鼓勵產業內部協同升級、非對稱併購的靈活運作。對以中型企業為主的臺灣產業而言,這是一種可複製的「從共生到共治」整併模組,極具政策推廣及實務操作參考價值。
本土案例:李長榮化工,從重創到私募重生的策略退場範例
李長榮化工的併購轉型,是一個典型的「危機後重組」案例。當年榮化歷經 2014 年高雄氣爆案重創公司形象與財務,後又經董事長更替與訴訟纏訟後,於 2018 年宣布接受國際私募基金 KKR 的併購提案,總金額達新臺幣 478 億元,並順利下市。此次交易的關鍵不只是私有化,而是透過「現金出場+家族保留部分股權」的方式,讓原股東集體獲利退場,同時保有原經營團隊對重建的參與。
此案也展現出併購過程中的幾個典型特徵:第一,採用「非對稱併購」手法,讓金主主導增資併購,創造流動性與策略重組機會;第二,家族股東兼任賣方與買方角色,體現私募基金與經營團隊共治架構的協調策略。若從併購法三修背後立法意旨在於促進併購之政策目的觀察,草案第 44-2 條有助於降低股份交換或重組過程中的稅務壓力,而第 52-1 條則有助於消弭小股東不同意而導致的流程延宕,讓這類私有化重組案更具可行性與市場操作彈性。
這場併購不僅讓一間歷經重大危機的上市公司得以重生,更提供了臺灣其他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一個參考模組:在合適的法制架構與資本配合下,退場不必然是代表結束,也可以是轉型重生的起點。
日本的國家級併購策略:從 INCJ 經驗看臺灣制度演進的對照面
在全球併購潮與產業整合變革中,日本於 2009 年成立的「產業革新機構(INCJ)」是一項具代表性的國家級嘗試。該基金由日本政府出資超過九成,結合多家日系大企業資本,以高達 1.9 兆日圓的投資規模推動策略型併購與創新型投資,意圖透過「產業整併 + 技術創新」的雙軌手段,改善日本長期以來的產業結構僵化問題。
這套模式有其成就,也有其代價。在執行面上,INCJ 以主導整併的姿態推動如 Japan Display Inc.(整併 Sony、Toshiba、Hitachi 的液晶業務)等案例,的確促進了資源整合與研發集中,但由於市場變化速度快、內部決策冗長,最終多數投資案未能實現預期效益。公開數據指出,INCJ 超過 80% 的退出案件出現虧損,反映出以「政策投資」方式處理市場問題的結構性挑戰。
與臺灣相比,INCJ 嘗試以投資收購方式集中破碎股權、重塑競爭主體,但缺乏靈活機制與市場動能支撐,成效相對有限。反觀臺灣《企業併購法》本次的修正方向,則是從制度層面鼓勵民間以產業控股平台實現整合,既兼顧彈性,也納入治理與稅務誘因,更適應新創與中型企業的升級需求。
INCJ 的案例經驗提醒:國家介入併購若僅止於資本控制,效果未必皆如預期;而制度性的誘因設計,引導企業主動參與意願才能真正促進產業整併、技術轉型升級的長期推力。
企業併購的三重價值
依據我的執行經驗,企業併購不能單純為了整併而進行,應該是基於企業價值之成長,為了商業模式之實踐,讓整體產業更有國際競爭力而進行之策略。從法律與產業實務來看,企業併購至少有三重功能:
1. 新創的退出機制:為創業者創造被收購、併入產業體系的現實出場路徑。
2. 大企業的第二成長曲線:透過收購策略獲得企業的第二成長曲線之技術或人才補強。
3. 產業升級的工具:推動成熟產業轉型,實現規模經濟與供應鏈再造。
若將眼光放深,《企業併購法》本次修法草案並不僅是技術性條文之修正,而是背後承載了對於產業重整與國家經濟轉型的意圖。尤其是草案第 44-2 與 52-1 條,雖看似技術性減稅與股權交易之手續簡化,但其背後代表的是臺灣如何因應全球反全球化浪潮的策略準備。
從「中小企業單打獨鬥」到「控股集團聯合出擊」,從「被動代工」到「策略卡位」,產業併購與整合不再只是大企業的權宜之計,而將成為臺灣能否站穩下一個世代經濟舞台的關鍵一步。
參考資料:
1. 國貿經濟服務網,《日本設立新官民基金「產業革新投資機構」》,2018.09.28
2. DigiTimes 《日INCJ 15年來投資成效如何? JIC接手聚焦IT與半導體》,2025.05.07
**創投律師 Bryan:https://bryan.law/